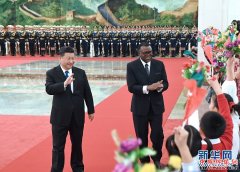白泉镇是一个民俗文化历史悠久的乡镇,不但孕育出诸如“海上锣鼓”“踩旱船舞”“跳蚤舞”“高跷戏”等民间艺术,并且涌现出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民间艺人,构成了海岛民俗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现在说说跳蚤舞。 一、百年四代传承 程琦,细溯上去,可以算是定海跳蚤舞的第四代传人,她直接师承于她的父亲———第三代传人程福清。程福清的师父就是跳蚤舞第二代传人何志福(1921-2008),而何志福则是由晚清时代在白泉教私塾的章孝善(1900-?)先生传授的。 民国十一年(1922)章孝善依靠自己的文化知识和超前的审美观点,把早已在舟山流行用于出庙会的跳蚤舞在内容上进行改革和提炼,让这一原本动作略嫌朴拙轻佻、形式上略嫌单调简陋的民间舞蹈注入全新的内容,从而焕发出勃勃生机。 据程琦介绍,章孝善以上的跳蚤舞直系传承人已不可考。但章孝善绝对不可能是创造跳蚤舞的开山鼻祖,现在的定海民俗民间艺术保护资料中往往称何志福为“第二代传人”,只是相对于他师承于章孝善而言。这是因为正史中对于这类民间俚俗表演不予记载,由于史料的缺乏,跳蚤舞的起源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何志福生前曾说过,跳蚤舞原是流传在海岛迎神赛会、喜庆丰收时表演的一种民间民俗舞蹈,但是由于迎神赛会和喜庆丰收的次数毕竟有限,这一类艺人为解决生计问题就利用这一技艺先是在每年的腊月廿三民间祭灶神仪式上作表演,以表示除旧迎新、祈求消灾免祸,故又称“跳灶舞”,再后来就会在富家之门或船头作表演以求点吃食,这种流行形式类似于“唱新闻”的民间艺人。他们的传承谱系自生自灭,在历史的风尘中早已烟消云散,没有踪迹可寻。 而何志福承认自己的先祖没有一个跳过跳蚤舞。他是11岁当学生时,在章孝善指导下开始学跳蚤舞,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知道,后来在庙会上表演了他们才知道,父母默认了他的这一爱好未加干涉,何志福有5个兄妹,自己的子女也有很多,但都不会跳,他也从来没有教过他们。 二、庙会上的跳蚤舞 白泉的白龙会一直是定海历史上最为兴盛的庙会。这种大型的庙会,百余年来历久不衰,人们喜闻乐见的跳蚤舞自然首列其中。 庙会上的各类技艺演出必须遵循一条规律,那就是必须是“行进式”的,就是一边走一边演,不可以停下来专门的演上一场,因为这样会拖了前进队伍的后腿,跳蚤舞也不能例外,所以这一阶段的跳蚤舞十分简单,所表达的主题也十分模糊,一男一女,吃吃豆腐调调情,女的打个大白脸,两腮涂得红彤彤的,鼻翼边上点个黑痣,一副“泼妇”搞笑模样,有时会一手提一只马桶(当然是没用过的新马桶),一手执一把“马桶洗帚”追打男的,男的也会提着一只俗称尿瓶的“夜壶”,时不时仰着脖子对着壶嘴喝上一口“尿”(当然是新夜壶装上清水)。那时女角也是由男人扮饰的,这样在调情时可以“放开手脚”,总之没有实质上的内容,纯粹是一种逗乐搞笑的甚至带有猥亵的动作。由于动作轻佻,形如跳蚤,故得此名。 程琦说,我们的父辈、爷辈就是继承和发挥了先辈历代传承下来的这些民间舞蹈艺术,并将它们保留至今,完全是依靠庙会这一载体。在全部的庙会演出过程中,这些艺人都是多面手,并不是单一地恪守某一项专艺。比如说我的父亲程福清本来就是敲“三番锣鼓”的,但他又会跳蚤舞,哪里缺人手就奔哪里。 当时塾师章孝善也是参加跳蚤舞的演员之一,这位颇有思想的当地知识分子对改进跳蚤舞有了一种冲动,他开始思考如何改革这一男一女演出的节目。并从“济公和尚斗火神”的故事中得到启发,开始构思节目的全新情节。 三、章孝善的创新和改革 《济公斗火神》的故事是这样的:云游四海的行脚僧道济(济公)在杭州的灵隐寺落脚借住,这一日寺里开光,灵隐内外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济公在寺外疯疯癫癫闲荡。不一会来了一位年轻的红衣女子要进寺烧香,那济公一眼识破是火神娘娘所化,知道她进寺后必要惹事生非,便左挡右拦不让她进。住持大和尚见济公不干活还调戏香客,不禁勃然大怒,厉声斥责。济公问住持:“师父,是有寺好还是无寺好?”住持想都没想回答:“当然是无事好”,济公一听,便放了那女子进寺,不一会,除了济公睡觉的那间柴房,整个灵隐寺便火光烛天,被烧得一干二净。住持师父这才追悔莫及。当然故事后边还有一段“济公重建灵隐寺”的精彩情节,那是不需要章孝善来表述的。 济公和火神,一男一女,一个要进寺,一个要阻拦,济公疯疯癫癫,动作自由,火神年轻亮丽,婀娜多姿,很适合作为跳蚤舞的表演内容。初期的表演是济公戴僧帽、着破僧衣,手持破扇,一闪左,一闪右,阻止女的前进;女角则穿红衣,挎竹篮,左一闪,右一闪,想方设法躲开济公要前行,具体在表演上以男角半蹲仰视着女角,作出戏笑的表情和阻拦动作,女角俯视男角,不停地扭动身子不时作出媚笑的表情和躲闪动作。配以锣鼓点节拍构成一驱一躲的意境。这一改革使节目的立意和主题就更明确,舞姿也更好看了。 在章孝善对跳蚤舞的改革过程中,何志福是一位忠实的实践者,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跳蚤舞自此在白泉一带名声大振,何志福的名气也大了起来。 程琦说,其实何志福和她家是隔壁邻居,在她的父亲程福清师承何志福、师徒之间切磋舞艺的时候,她耳濡目染,爱上了这一行,因此也常受何志福的点拨。但何志福无论从年序的排辈上,还是从师承的谱系关系上,她都应该称何志福为“爷辈”或“师公”。何志福之所以成为跳蚤舞的名艺人,一是得益于他与章孝善非常明确的师承关系,是章孝善的得意门生;二是章孝善对传统的跳蚤舞进行历史性的改革全部通过以他出色的演艺来实践并取得成功;三是何志福有幸从旧社会跨越到新社会,继而又跨越世纪,国家对民俗艺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培育环境,让他继承并发挥了他的这一门技艺。 新中国成立后,何志福收了不少的徒弟。但庙会作为封建迷信被取消了,有着鲜明地方特色的跳蚤舞包括其他诸如海洋锣鼓、舞龙、踩旱船、高跷等便都失去了表演的平台,白泉镇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乡镇所包涵的这些大量传统民俗演艺形式包括多才多艺的民间艺人,亟需寻找一个展示的平台,而老百姓也确实以怀旧的情结渴望能重睹这类表演的昔日风采。因此,跳蚤舞先是以舞台表演形式重放了它的异彩,继而通过民间的智慧创办的“白泉振兴会”以一种全新的角度重现了一把昔日庙会的盛况,让这些艺人和当地老百姓大大过了一把瘾。嗣后,白泉镇首创了名目繁多的各种“节”,集中地为民间艺术提供了一个表演平台,“跳蚤舞”自然首当其冲。 四、跳蚤舞的又一次改革 跳蚤舞没有台词,没有唱词,完全依靠两人夸张的肢体语言和滑稽动作吸引观众。1953年,会跳“跳蚤舞”的何志福受邀在全县各大乡镇礼堂首次演出,这也是跳蚤舞由庙会表演首次转向舞台上演出,他饰演济公,当时扮女角的对手是章孝善的儿子章新华。演出相当成功,一时之间他成为解放后作为民间文化交流演出的明星。 相对于庙会“行进式”的表演,“舞台式”向表演者提出新的挑战。何志福首先考虑到女角是否可以用女性来扮演。因为一直以来,女角都是“男扮女装”的,“男演女”动作幅度和刚性有余,温柔美感不足。1955年,舟山地区文化馆指名《济公阻火神》的跳蚤舞节目参加在杭州举行的全省第一届民间古典音乐舞蹈观摩演出。为提高节目的质量,何志福趁机提出“男女合演”的建议,得到领导的支持,选派了普陀沈家门女子张雅珠作为他的搭档。这也是一次跳蚤舞“史无前例”的改革,何志福既演男角,又指导张雅珠的表演,适当地收敛了以往一些过于夸张、轻佻的动作,以减轻女角动作幅度和心理压力,同时充分发挥了女性妩媚、婀娜的特点,让火神娘娘竭尽一种“勾引、风骚、吊翠、娇嗔”的表情和体态,既保持主题的原汁原味,又增强了美感和旋律,达到雅俗共赏效果。经过半个多月的反复加工和排练磨合,加上女角张雅珠的舞蹈功底,这次全省级的演出,在60多个节目中脱颖而出,获得巨大成功,节目得一等奖。自此之后,“男女合演”就成为定例。程琦说,倒是后来因为男角少,也曾出现过“女扮男”的形式,不过这些都是临时替代的权宜之计,正式演出时一律都是男女合演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何志福已年逾花甲,尽管他舞姿娴熟,但上台表演已力不从心,更多的是向弟子们进行指导和传教,带徒传艺成了他全部生活内容。他所带的弟子,既有男角,也有女角。程福清就是何志福众多得意弟子中演男角的弟子之一。2008年何志福辞世后,程福清继承了何志福跳蚤舞的全部精髓并有所创新和发展。程福清说,其实跳蚤舞的男角在表演过程中在体力动作上远比女角要更吃力。首先男角自始至终都是以“蹲马步”的形式进行表演。“蹲马步”是武术中的一个基本功,要求双膝微屈,上身挺直,然后再加上规定动作。程福清认为,创新是民俗文化的生命源泉,跳蚤舞也不例外,因此他不断尝试如何对跳蚤舞进行创新改革,让它更适宜在舞台上的表演,突出主题,增加美感。例如后来他在济公的服饰上添置了酒葫芦、佛珠、木鱼和破扇,在动作上增加了以颈“甩”数珠、原地板、斜角板、拱头板、跳脚板、折腰板、跳脚双手拜和敲木鱼等“八大套”内容,每套动作都要在舞台四角兜圈子,这些都是以往庙会上没有的,而女角的动作相对要自由一些,展现的是女子流畅柔韧的体态和灵活多样的动作,如添加手持花伞、手绢的旋转,花伞的旋转等。最基本的一点是,两人自始至终都必须“四目相对”,其间的“戏笑”“媚笑”“挑逗”“勾引”“色诱”“嗔怒”“假踉跄”“真护花”,男角的“谄笑、傻笑、耸肩、抹脸、挤肩、弄眼”等都必须在动作表情中体现,若不能亲眼观摩,殊非一言能尽。 五、培育全新的一代 时光流逝,岁月递易,转眼之间,程福清也年届耳顺,所庆幸的是跳蚤舞世代传承有望,他的子女大有父亲遗风,甚至包括他的妻子都对跳蚤舞这一民间艺术非常热爱。长子程勇、次女程琦,本身就是一对舞伴,有时人手不齐,母子之间、父女之间也时常搭档演出,这在白泉镇各社区是尽人皆知的家庭舞蹈队一家子。程琦15岁时在父亲程福清的指导下开始学跳蚤舞中的女角,爱美的小姑娘大大过了一把用重彩化妆成美女的瘾。但她还是认为,作为舞台演出的节目,一个“美”字是最重要的,跳蚤舞已经从草野台子走向舞台,而在高科技的灯光和音响条件下的舞台演出唯恐不美,要越美越好。随着演出次数的增多,她对跳蚤舞的创新问题也有了自己的理解。火神原本盘头式的发型太过简单,她首先在女角的头饰上作了改动,亲自用闪亮的珠子扎成极为亮丽的头饰,并根据火神的特点在眉间画上火焰的形状,突出火神的人物特点,又改窄袖为水袖,改手持手绢为彩扇,改济公手执破扇为双手执彩绸扎成的短棍等,不断寻找最漂亮的有表现力的道具,这些创新得到观众的认同,让大家百看不厌。 程琦的创新还表现在对配乐的改革上。跳蚤舞除了演员的肢体动作外,舞台上的音响只有打击乐,即锣、鼓、呔锣,钹子,这几种打击乐器根据需要,有多有少进行配置,击打出不同的乐律,演员要根据这些乐律进行舞蹈动作,不可越雷池一步。由于演员没有台词和对白,更没有唱腔,声音短促的打击乐不免单调,因而整体连贯性不强,程琦试着在打击乐中加入民族乐器唢呐,用高亢的唢呐声串联打击乐的间隙,这样一来不但体现喜庆的气氛,且配乐层次更为丰富雄浑,使舞台效果十分显著。 时至今日,跳蚤舞从单纯的庙会表演走向舞台。而政府对民间文化艺术的日渐重视,跳蚤舞的传承基地也纷纷建立。 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程琦,让她有了一个向娃娃们传授跳蚤舞这一民间演艺的广阔平台。2003年起,她每年在新入园的幼儿中开设跳蚤舞这一特色课程,从中选拔具有舞蹈天赋的苗子进行系统培养,然后编入幼儿园跳蚤舞队,不断向社会输送人才。 程琦还在这一块“试验田”里尝试改进传统的模式,赋予跳蚤舞以更多的新鲜元素予以创新。比如在人数上,她打破以前只有男女两人表演的局限,发展到两对(四人)舞、三对(六人)舞、四对(八人)舞甚至更多人的集体舞。这足以说明,在定海流传了近百年的这一充满激情和魅力的民间古老舞蹈终于有了传承基地并后继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