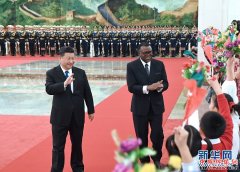|
2016年的春节,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的乡村图景》的文章传遍了朋友圈,继2015年王磊光的《博士返乡笔记》之后,知识分子的返乡书写再次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公共话题。但对于作者黄灯来说,这篇文章并不是所谓的“返乡体”,不是一年一度的春节返乡随感,而是她对家族历史的梳理,是她多年观察的一次偶然出场。由这个视点出发,她又将目光投向了与她生命产生关联的三个村庄:丈夫的老家丰三村、自己的出生地凤形村、和外婆生活的隘口村,对这三个村庄的回望和关照构成了她的新书《大地上的亲人》。 作为整个家族里唯一一个获得高学历的人,黄灯的成长经历,隐喻了一条逃离乡村的路径。然而堂弟的一次偶然造访,却打破了她隐匿城市、沉湎学术的平静生活。一切还要从2002年的中秋说起,彼时黄灯还在广州读博士,在广州打工的19岁堂弟敲开她宿舍的门,兴奋地告诉她,自己如何巧妙地躲过门卫的盘查,进入神秘的中山大学。堂弟的手里还拎着一盒“广州酒家”的精装月饼和一箱蒙牛牛奶。 黄灯坦言,堂弟的造访对她的冲击,就好像鲁迅在仙台医学院看到国人围观屠杀同胞的幻灯片。她开始反思,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中,逃离乡村的群体,是如何在知识的规训中,以个人成功的名义剥夺一种本真的感情,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精英的感觉,逐渐疏远身后的亲人。一个出身卑微、年幼丧母的孩子,在戾气横生的坚硬现实里、在广州多年的心酸辗转中,都没有磨灭悲悯与爱的能力,她又有什么资格,每天坐在条件优渥的办公室里,写一些不知所云的论文,让知识稀释了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情感。 因此,对于黄灯而言,书写乡村,书写自己的亲人,首先是一种自我清理,她试图在书中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和她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建立一种关联,“农村滋养了这么多人才,贡献了这么多资源,作为一个城市里的农村人,应该想办法回馈农村的父老乡亲。现在城市里的中产,面对困境一个最直觉的反应就是移民。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我,逃离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是完美的解决方案,逃得开这个地方,逃不开你内心的困惑。我觉得还是要有人留下来,建设我们的家乡,守护我们生存的土地,解决我们实实在在的问题。” 其次,作为一个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黄灯也明显地感觉到,现在很多作家的生活越来越同质化了,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是名牌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就立即进入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和资源,利益团体很快就形成了。而另一方面,我们整个社会的异质性却越来越强了,转型期社会对抗的激烈程度没有办法进入作家的视野,因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圈子之间的隔膜太严重了。因此,如何进入乡村,呈现乡村,与乡村建立关联,也是知识界必须清理的问题。 在黄灯看来,这本书既有别于纯粹的文学写作,也不同于专业的学术著作,加之作者与叙述对象之间的情感牵连,也使得她很难滤除掉其中的主观色彩,但这一切都不妨碍这本书的初衷,那就是在问题推动下的真相呈现,是知根知底的表述:“如果说农村病了,我就是一个写病历的人,我只能尽力把病历写得完整一点、真实一点,至于开药方,我还没那个资格,要交给三农专家们去做。” 界面文化:这本书收录了你从2003年到2016年的文章,你是一直都有写这样一本书关于家乡、关于中国乡村的书的想法吗? 黄灯:我的确是从03年就开始写一些关于农村的文章了,那时是用一个文学青年的笔法在写。从06年起我就已经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了,我在“天涯”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的文章,写的就是我的老家。那时我最想写的是我家乡的乡亲在南方打工的故事,那个对我的冲击是最大的,我出生的村庄里每家每户都有人在南方打工,这些人的离开,彻底颠覆了整个村庄的结构。这本书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确实是酝酿了很长时间,是因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以下简称《乡村图景》)这篇文章,才让我有一个契机,把这么多年的想法表达出来。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成长对你来说就是不断逃离乡村的过程,那你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主动亲近、关怀和回馈乡村的呢? 黄灯: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觉得我会一直在农村生活下去,我特别向往外面的世界,又很喜欢读书,从书本里面接触到的世界跟现实世界的差距非常大,我很向往那种精神性很强的世界。所以对我来说,走出农村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后来出去读书了,对于农村人来说,如果你出去读书了,他们就会把你当成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就会觉得他们的生活跟你没有太大关系了。后来我到广州去念博士以后,又有机会跟那些来广州打工的亲戚在一起,目睹了他们的生活,就觉得我们就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只是我们来到城市的方式不同——我是通过读书,而他们是通过打工。以前城乡的二元体制更僵化,农村人都没有机会出来打工,只能守着老家,来自一个村庄的不同人群又在同一座城市团聚,这样的现实也促使我思考。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多次提到,这本书的写作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还引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宁可因求真实性而牺牲普遍性”,如何理解乡村书写中真实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张力? 黄灯:《乡村图景》发表之后,我也听到一些批评的声音,很多人批评说我写的只是一个个案,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乡村的境况。我自己肯定也知道,一篇文章不可能把中国乡村整体的境况展现出来。因为这篇文章的影响大,很多人就会认为里面的内容代表了中国乡村的普遍状况,实际上,我自己写作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意图,我知道我写的只是个案,只能代表我的家庭。所以对于写作者来说,我更注重一些细节、肌理,而不是刻意去寻找一些结论和框架。这就是我理解的真实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写作的目的,不是要得出一个结论,而是要呈现真相,让大家看到现实是什么样的,而至于现实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以后会怎么发展,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够解答的。在我看来,丰三村(注:黄灯嫁入的中原村庄)和凤形村(注:黄灯出生的湖南村庄)的状况还是可以代表大部分中国村庄的,是有一定普遍性的,但是这种普遍性是没有一个先验的结论的。我不觉得中国的农村研究只有一个模板,只能得出一种结论。 界面文化:你曾经在一篇反思返乡书写的文章中提到,你经常在反问自己,隐匿城市与知识为伍的生活与亲人在乡村生活中的挣扎和困顿,究竟哪一种才是你需要面对的真实,这可以代表成功“逃离”农村的“农二代”的普遍心态吗? 黄灯:我觉得是可以代表的。我在广州的时候,每天面对一些学院派的知识分子,跟学生、老师、媒体打交道,我会觉得我的生活就是一种知识化的生活,但是我每次回老家的时候,面对你的父老乡亲的生老病死、吃喝拉撒,是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人就会觉得生活是错乱的。因为事实上,老家的生活是无法摆脱的,即便在城市里,与故乡的联系也是割不断的,比如你要定期打电话回家询问家里的情况,家里有没有人生病,需不需要钱,只是这种生活在平时隐匿于城市生活之下,对我来说,它们是同样真实的。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多次提到农村婚丧嫁娶的高昂花费,作为人生重要的仪式,婚礼和葬礼在村民的生活中主要产生了那些意义? 黄灯:以前的意义是跟传统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现在是跟消费主义联系在一起。一个农村人在外做一些很苦很累的工作,并不单纯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为了争一口气、挣个面子。如果他的婚礼特别热闹,那在整个仪式之中,他就确认了他的价值,乡亲们都对他另眼相看,觉得他很风光地把老婆娶回来了。他的人生价值来自于别人的认同,而这种认同的标准又来自现在流行的消费主义观念。 另外,结婚和生育依然是农村人一生最重要的事,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也没有别的压力,不像读过书的城里人,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都不重要。现在的90后婚育年龄都大大提前了,一个男孩子到了二十二三岁,如果还没有对象,村里人基本就认定他找不到对象了,女孩子倒没这个问题,因为男方娶亲的成本太高了,男女的择偶标准都严重地物质化了,就是双方把各自的条件摆出来,由媒人在中间做媒,如果大致觉得还看得上眼,婚期马上就定下来了。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写到,现在农村的社会保障主要依靠熟人社会中的家庭成员互助,这种模式的脆弱性在哪里? 黄灯:以前子女很多,总会有个把情况好些的,现在孩子少了,最多两个,所以以后就只能靠社会了,现在农村的社会养老也比以前好了一些,虽然钱很少,6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有几十块钱,但是对于农村人来说,自己有房子住,能种地有粮食吃,几十块用来买点油盐,也还过得可以,反正他们要求非常低,只要能活下来就可以了,不需要别的享受。 界面文化:您在书中写到现在村里的农民种地都不用自留的种子了,而是向跨国公司买种子,我看到很多学者也在关注这个问题,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问题,也是一个粮食生产主权的问题,能具体讲讲这个问题吗? 黄灯:我小时候,在我外婆家,自己种的菜自己肯定要留一棵。如果种黄瓜,就会自己留一条大黄瓜,让它长得很熟很熟,就把种子留下来了,放在屋檐下晒干,但是现在没有了。我很长时间以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只是觉得菜越来越不好吃了,我就去问我妈妈,现在的菜为什么没有小时候好吃了。她说现在的种子都是从种子公司买的,买的种子又不生虫、产量又高、长得又快,但是这样结出来的果实是没办法留种子的,而且留种子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风险也很大,万一我留的那条黄瓜被人偷偷摘走了怎么办,被老鼠吃掉了怎么办。种子的保留期又很短的,老种子最多能保留一两年,所以现在老种子基本上的绝迹了,只有在一些特别偏僻的山区,跟外界没什么接触的农民,还保留着留种子的习惯。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也提到了农村基层组织和集体生活的缺位,很多村民甚至会怀念集体经济时代,认为有好的领导,带领大家搞集体经济才是农村的出路,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灯:现在农村的社会组织基本上彻底溃散了,村干部和村组织对农民是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的,以前的村组织是很有机的,财产也是属于集体的,所以号召力是很强的。我觉得农村要想发展的话,还是要组织起来,没有组织的话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比如说公共卫生,现在农村的污染很严重,垃圾和农药对水和土壤的污染都很严重;还有很多新建的房子的下水道,都是各家各户自己挖一道沟,污水都是随处乱排的,虽然房子都很光鲜,但是只要稍微追问一下那些污水都排到哪里去了,就觉得不堪设想,这些问题是必须通过一些公共机构来解决的。90年代的时候,村政府主要负责收税,抓计划生育,公共服务提供得很少。现在在公共服务方面好一点,因为现在是国家拨款,村政府负责把这些钱分到每一个农户头上去,但这又带来了新的矛盾,甚至比以前还多,比如怎么认定贫困户,就像去年的杨改兰事件,就是这个问题。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将进城务工的“农二代”和城市蚁族做比较,认为他们又形成阶级联合的可能,你认为这种联合的可能性在哪里,困难又在哪里? 黄灯:可能性就是阶级接近。我在大学里面教书,我的很多学生毕业以后所面临的问题和我老家那些没读过书的打工者是一样的,但是那些读过书的孩子会觉得他们不一样,他们可能不愿意去跟打工者联合,他们不甘心,认为“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凭什么说我跟你一样”,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境况真的差不多。因为即便你是大学毕业,但如果家里没有更多的资源,那大学文凭的含金量也打折扣了,甚至需要自降身价,才能找到能养活自己的工作,所以说我觉得“蚁族”这个群体真的是非常尴尬的。我在书里写到一个例子,就是我大姐的大女儿,是读过大学的,她的三女儿可能小学都没毕业,最后她们两个住在一个小区里面,找的老公也都是在外面打工的,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她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差别。 界面文化:在一篇对您外甥女的访谈中,她提到她不喜欢看写打工者生活的《佛山文艺》,反而更喜欢看写城里人生活的《读者》。您觉得打工者自己的创作和自己办的刊物,在打工者中间真的有市场吗? 黄灯:我在广州上班的时候,我就喜欢看《佛山文艺》,因为那些打工者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很陌生,所以当我听到她这样说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说明人换一个视角,看问题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她从内心觉得《佛山文艺》太土了,写的都是工厂的生活、宿舍的生活,在她看来太日常了,她觉得她要看一些《读者》这样的心灵鸡汤,能够满足她对生活的幻想和另一种期待。 所以我觉得可能像《佛山文艺》或者皮村那些工友的作品更多地还是知识分子在读、在研究它们,知识分子迫切地需要这些第一手材料。比如那个叫李若的女孩子,是皮村里面写的非常好的,她的作品几乎是没有任何虚构的,是可以作为可信的研究材料的。至于这些作品在和他们同一阶层的人看来怎么样,这个就很难揣测了。 界面文化:你在书的最后提到,乡村建设的一条可能出路是从当地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中汲取养分,可以具体讲讲吗? 黄灯:我主要是从隘口村(注:黄灯外婆生活的村庄)近几年的变化中受到的启发。隘口村所在的镇叫做长乐镇,长乐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以前是岳阳的首府所在地,岳阳城的历史都比不上它,因此有很多传统文化,比如说“玩故事”(“玩故事”又称“故事会”,是长乐流传了几百年的民俗形式,内容以民间传说为主,包含了忠孝节义的价值传播;形式以台阁展示为主,通过上下街的竞争对垒产生故事, 充分调动了普通村民的热情),从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很流行了,而且一直没有中断。“玩故事”是一个集体活动,不像是一种技艺,只能传给少数人,它是几百人共同参与的活动,每家每户都要参加。一个地方常年受这种集体生活的影响是会产生一种精神的,所以长乐镇的农民性格和其他地方的农民很不一样,组织性特别强、很团结、很讲义气,也爱虚荣、爱面子,活色生香的,每个人都很“有劲儿”,有那种很质朴的、粗鲁的原始生命力。但是这种生命力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指引的话,是很容易导致很多极端问题的,所以在90年代,那里吸毒、赌博是最厉害的,这和那里的人感性、不怕事、喜欢刺激的性格分不开。 但是从2010年开始,我感到村子的风气明显在变化。新农村建设以来,很多钱拨到村里,给村里修了很多公共场所。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面,每个村子都有很多公共场所供村民们集会,比如晒谷坪就是村里人活动的公共空间,每家每户在那里晒谷子,小孩子在那里玩耍,晚饭后所有的妇女都聚在那聊天,但后来公社解体之后,晒谷坪就被瓜分了,用来建了很多房子,村里也就没有公共空间了。2010年开始,村里又重新建起了文化活动中心,村民们就开始自发组织腰鼓队、跳广场舞,这些集体互动多起来了之后,打牌的风气自然就淡了。后来腰鼓队还到北京来演出,“玩故事”也申请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村民们的虚荣心就调动起来了,村里的风气就转向了。像隘口村这样的村子,如果从传统文化方面来引导的话,其实还是很有希望的。每年在大广场上几千人一起“玩故事”的时候,如果有社会力量介入,做一些演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责任编辑:陈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