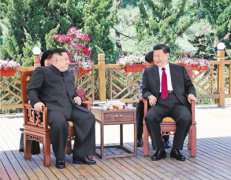|
尽管谁都明白承包地分散细碎的弊端,呼吁“互换并地”实现连片规模经营,但提起土地整合,很多人还是直摇头——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动一分一厘,都可能引发大纠纷,谁敢贸然打破延续几十年的既定利益格局,去捅这个‘马蜂窝’?” 但在广东省清远市,短短两年,全市一半耕地完成置换整合,重新按户连片发包。全市涉农矛盾纠纷不升反降。 同样,谁都明白村庄内部公益事业是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突出问题,都疾呼“没有农村内部主体性力量的激发,农村改造和改变难以持久”,但提起税费改革后农村公益事业兴办的难题,很多人还是直说头疼—— “沟不挖到自家地头,路不修到自家门口,就不参加筹资筹劳。只要有一两户想搭便车,别的农户肯定又把钱揣回兜里。” 但在湖北省秭归县,村级公益事业却已经风生水起:3年全县农民自筹资金6200多万元,新修公路1115条3688公里。过去很多“一议就黄”的流产项目,如今村民“聚到一起一叨叨”,群策群力中便呱呱坠地。 地还是那片地,人还是那群人,曾经的“老大难”何以“难者亦易矣”? 一团乱麻,关键是找出线头。清远、秭归虽然相隔千里,但似乎心有灵犀,理出的“线头”惊人相似:划小村民自治单元,激发基层创造力与活力,让农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这“线头”,乍一看并不起眼:无非就是通过对自然村这一传统资源的挖掘,在建制村以下开拓出村民自治的空间,让“十几公里外的事”变为“家门口的事”,让自治进入“微观”和“细化”的具体层面。 然而,真正走进田间地头细打量,确实非同寻常:不随“合村并组”的大溜,以村民小组(村落)为自治单元的“微自治”探索,蕴含着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课题。 大村庄的弱自治 “上面的刚性任务完不成,下面的自治事务就得缓一缓” 秭归的“线头”,是从王家桥村牵出来的。 九曲十八弯,山路盘旋,满眼柑橘树。地处三峡工程坝上库首的秭归县是脐橙之乡,王家桥村在当地名气不小,是水田坝乡数一数二的红旗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向富柱当了三十来年村干部,治村有“几把刷子”,但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 这回让他心力交瘁的,是一条小村道,从村南头往北接通村部,区区2.4公里。但它来头不小。2012年,秭归县精品果园核心试验示范区建设项目落户王家桥,项目投资上千万元,配套建设的这条路,由村委会牵头实施,涉及几个村民小组的78户人。 “认了三个干妈,讲了无数好话,3年磕磕绊绊修通1.7公里,到现在还是条断头路!”向富柱脱口而出一首自创的顺口溜:“过去修路要征地,每亩投资两万一,给了补偿还扯皮,搞得不好堵挖机,抽调一个副书记,受了不少窝囊气,至今问题没理清。” 村民心里都清楚,要脱贫,先修路。路是共同的利益诉求。山高坡陡,田间地头不通路,采摘橙子就得一篓一篓地背回来,效率低、成本高,“人老体弱奈不何,请工一天一百多,卖斤橙子少一角”。 然而,面对政府项目“下村”,不少村民的第一反应不是如何参与,让好事落地,而是“项目来了,就等政府发钱补偿”。村民向昌凤的话,道出一种普遍心态:“占了我家地,砍了我家苗,能补4万要8万。你来做工作,让我带头让一让,凭啥子?” 村委会专门雇了3位村民协助化解施工阻扰矛盾,并召集村民开过4次会,结果都是各说各话、吵吵闹闹,计划中的最后几百米不了了之。 为什么群众参与难组织、公益事业难办成、社会服务难到位?王家桥村的断头路,引起前来调研的宜昌市、秭归县领导的深思。 “建制村治理单元偏大,随着村民诉求多元化,利益协调难度加大。”秭归县民政局局长宋正荣分析说。2000年秭归“合村并组”后,建制村地域范围平均达到13平方公里。同一个建制村里,村落分布下起江边、上至山顶,海拔落差1500米以上。山下种了柑橘的农户想修路,山上普通的农户则需要起码的产业,“都是眼皮底下的事情最重要,对建制村范围内的其他公共事务,村民关注度、共识度低。” 秭归农村面临的问题,广东清远干部感同身受。 清远是山区农业大市,居住分散也是当地村庄的典型特征。“清远最大的村,面积50多平方公里,有71个自然村8000多人。”清远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农办主任鲁小鹏说,“有些村干部从当选到任期结束,有村民连面都没见过。” 2012年,葛长伟就任清远市委书记后,大半年里跑遍全市85个乡镇、200多个村庄调研,梳理了当地村民自治效果不明显、农村不稳定因素较多等六大问题,“这些问题,最终都汇集成一个:农民组织化程度低。” 在秭归,村民同建制村之间还有“土地属于集体”的联系纽带;而在清远,90%以上的村庄,集体资产和经济事务都掌握在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一级,缺乏共同利益,就没有参与动力。清远市委副书记黄兆芬说,产权与治权脱离,村委会很难把没有资产、利益关联的村民统一起来达成一致行动,自治功能就有“悬空”之虞。 “行政与自治功能冲突。”在鲁小鹏看来,这是不少地方“农民个体化”、自治难落地的症结所在。 在清远市阳山县黎埠镇鲁塘村,村支书肖裕捋了捋,村干部要承担“各类业务报表按时上报”等130多项职责服务事项。 “村一级承担的任务中,哪些属于‘行政化’工作,哪些属于‘自治’事务,说实话,还真不容易搞清楚。”秭归县水田坝乡党委书记廖厚坤说,我国政府机构设置到乡一级,村委会属于自治组织,但各级任务落实不能没有“脚”,“上面千条线”最终还是要落在村干部“下面一根针”。 宜昌市有关部门去年开展的一项调研显示,秭归县茅坪镇陈家坝村要承办县和镇两级16个部门的41项工作。当年上半年,村干部先后完成新农保新农合费用收缴、商业保险、企业普查、残疾人普查、低保复查、计划生育检查、地名普查等10多项事务性工作,占了2/3的时间和精力。面对村干部的忙与累,调查显示,有30%的村民认为村委会是镇政府的“代办所”、村干部是镇政府的“腿和脚”。有村民说:“村干部是忙,但不是为我们忙,是在为上面忙。” 一边是每村3到5名的村干部职数,一边承担着不下百余项的行政事务,村委会行政化问题凸显。一些村干部表示:“上面的刚性任务完不成,下面的自治事务就得缓一缓。”“村干部辛苦跑断了腿,堵不住百姓埋怨的嘴。”
葛长伟坦言,从清远的情况看,以建制村为单元的基层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农村发展和社会治理需要。 小村落的新变局 重构乡村共同体,让村民自治从“十几公里外的事”变为“家门口的事” 清远的“线头”,是从叶屋村牵出来的。 叶屋是英德市石牯塘镇萤火村一个偏远自然村,35户人家,同宗同源都姓叶。 这里曾几近凋敝,村民大半外出务工,撂荒耕地50多亩;如今,机耕路四通八达,耕地、鱼塘连片,外出打工的村民基本回来了,连“瘦田”都争着要。人均年收入从2009年的3000余元,跨越到2015年的3万多元。 叶屋蝶变,关键是村中“传奇人物”叶时通和以他为首的村民理事会。 叶时通50多岁,虽只有初中学历,但脑子活。1998年,他拿自家的4亩良田跟别人换了7亩地下渗水的差地。笑话他“傻”的村民,很快瞠目结舌——原本分成12块的碎地连成一整片,叶时通挖了两口大鱼塘,周边养上猪,头一年就净挣4万元。 爱折腾的叶时通又“异想天开”,打起全村土地的主意:“把分散经营的土地整合后统一丈量,再重新调整分配给村民。” 这主意并非不接地气。1981年叶屋将集体土地按照质量平均分给农户,户均10.6亩,有11处地块。当时村内最大的一块连片耕地也不过5亩。地块小,这家种菜一打药,旁边种桑养蚕的就深受影响。 这主意却又真不接地气。尽管当了多年村民小组长,口碑好、威信高,可好几年的村民大会上,无论他如何“舌灿莲花”,终是应者寥寥。一涉及切身利益,谁都怕自己吃亏。 “撞了南墙”,叶时通也不回头。他想过找村干部出面做工作。但萤火村一共有22个村民小组,5名村干部忙得无暇顾及,更有顾虑:“村干部分属不同村民小组,不同姓,叶屋村民对同姓的叶时通都不完全信任,外姓村干部就更没办法插手了。” 萤火村党总支书记李锦都记得,之前村“两委”曾想在叶屋修条路,劝村民让一些地,被一口拒绝:“你们村干部是不是‘进水’(贪污)。现在搞建设,你们又有‘水’进了。”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叶时通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村内同族各房、有影响的5名代表,成立叶屋村民理事会,推行土地整合。叶时通被推选为理事长。 打亲情牌,各个击破,“理事”话事,就是不一样。2009年开春,一场全村总动员的土地互换调整在叶屋推开。 但整合远比预想的艰难,丈量过程中,有动摇反复的,甚至有扬言砍人的。“要想不打起来,先得自己站出来。”叶时通率先将刚投资2万多元建好的3亩鱼塘交给村民小组。 组织了30多次村民大会,历经无数次争吵场面,叶时通与村民理事会成员一起,终于在2010年春完成全村土地整合,彻底解决了困扰村子30多年的土地细碎化问题。 叶屋的草根创新,让清远市委清楚地看到了调动农民积极性、主体性、参与性,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突破口。葛长伟说,在一个村民小组,很多村民都属同一个家族宗族,血缘关系、利益联系紧密。村民理事会组织群众协商,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党委、政府再加以引导,比自上而下去推动效果要好得多。 2012年底开始,在不断吸收叶屋等村首创经验的基础上,清远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2+7”系列改革配套文件,力推党组织建设、村民自治、农村公共服务“三个重心下移”,探索以村民小组(自然村)为自治单元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党组织的设置,也由“镇党委—村党支部”,调整为“镇党委—党总支—党支部”,支部建到自然村一级,激活了党组织的“神经末梢”。 村民自治“下移”至村民小组(自然村),以自然村为单元选举成立村民理事会16412个。同时,以3个镇为试点,探索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自治单元,成立村民委员会,重构乡村共同体:将现行的“镇—村(建制村)—村民小组”调整为“镇—片区—村(原村民小组、自然村)”,下沉后的村委会不承担行政化事务,集中精力做好自治工作,在原建制村(改革后称片区)建立村级社会综合服务站,人员主要由原村“两委”成员担任,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与清远改革遥相呼应,秭归自2012年开始,总结王家桥村民自发创造的经验,在全县范围开展“幸福村落”创建活动,探索在保留村民委员会管理框架的前提下,创新设计农村治理组织构架。 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相通、群众自愿、规模适度”等原则,全县186个建制村的1511个村民小组,被划分为2055个村落。每个村落规模在30到50户、1到2平方公里范围。 在村落治理的组织体系上,实行“双线运行”,即“村党总支(支部)—村落党小组—党员”为主的党的基层组织体系,以“村委会—村落理事会—农户”为轴线的村落群众自治体系。村落理事会因需设职,因职选人,设立理事长、张罗员、调解员、监督员等“一长八员”。他们由村民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产生,属社会组织成员,以义务方式履职。 “大单元”变身“小范围”,自治下沉,前路如何?
微改革的大效应 让群众说服群众,让群众带动群众,政府归位、自治到位 同样是王家桥村,同样是修路,境遇迥异。 过去,国家投资,工程没动,征地先补偿村民50多万元,最终3年修了条1.7公里的断头路。如今,不向政府要一分钱补偿,村民占地互调、砍树互补、资金自筹,3年修了7条、12公里果园路。 建制村失灵的地方,在自然村咋就灵了?面对我们的困惑,向富柱与王功勋相视一笑。王功勋是王家桥村第七村落理事会的帮扶员兼宣传员。 “向书记他们乡村干部能做的,我们群众代表做不了;但有时我们群众代表能做的,向书记他们水平再高也未必做得了。”王功勋哈哈一笑,讲起了故事。 商量自筹资金修柑橘果园路之初,王功勋组织26户村民开了七八次会,最后一个“钉子户”终于签字同意。不曾想,第二天他又变卦了,要求提高补偿。 “既然你不出钱不出工,那么路修好之后你不能用!”王功勋撂了“狠话”。 路照修,只是路线变了,绕开“钉子户”家果园。这下他急了,登门来找王功勋。轮到王功勋“摆谱”了,“我跟他说,这事是当时所有村落群众决定的,我不能擅自更改,你要想加入得去找大家伙儿说。”他只好挨家挨户上门求情。“大家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最后补缴修路款后还是让他加入了。” 王功勋说,村民之间都是熟人,沾亲带故,互相间有约束,所以理事会能制定一些土政策或土办法,做成以前村干部乡干部想做却做不成的事。 “公益事业好办、社会风气好转、干部工作好做。”秭归县委书记卢辉认为,凝聚村落的自治力量,改进自治方式,让农村基层治理更上一层楼。在村落理事会,充分继承传统乡村治理的合理内核,一批能人、贤人、明白人、热心人脱颖而出,全县一支超万人的队伍参与乡村治理,极大改变了过去光靠700多名村干部撑着的局面。 秭归县民政局工作人员李林修讲的一件小事让我们印象颇深。九畹溪镇界垭村第十一村落,李某张某两家因山林四界闹了20多年矛盾,打骂闹斗,甚至动过刀。镇派出所、司法所、村委会多次调解,都没成。“以村委会为大单元的村民自治,大道理好解决,小问题特别是涉及微观层面的问题难以协调。” 成立村落理事会以后,调解员主动站了出来,拿出自家20多年以前分地时的四至记录,当面锣对面鼓地指出了两家土地面积大小,想占别人土地的张某自知理亏,就此罢手。调解员的妻子担心得罪张某,埋怨他多管闲事。“你比哪个夯实些?”“不是我充夯实,既然大家把我选出来,说明信任我,我必须主持公道!” 自治单元下沉,产生的“化学反应”连锁变化,让一些基层干部始料未及。 现任清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伍文超,不久前从阳山县委书记任上提拔上来。阳山2014年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心直口快的伍文超对市里“先整合再确权”的要求直接“抗议”:“这个事要是领导不怕上访,就能搞成功,怕上访就成不了!”他的想法和当时大多数干部一样,认为土地互换整合没有国家法规的支持,不能强制实行,难度“比计划生育还要大”。 硬着头皮接下来后,伍文超到几个村住了一段时间,与农民一户户谈,发现群众对土地整合其实是欢迎的,关键是要转变“上对下”的工作思路。“党委政府不大包大揽,充分发挥村党建和村民自治重心下移的作用,让群众说服群众,让群众带动群众。”伍文超心里逐渐有底。 刚开始,江建青心中也没底。他是阳山黎埠镇升平村前锋、四新、联合3个村民小组选出的村民理事会理事长。接到村里土地置换整合的求援电话,他放下在外地的工程专程返乡。召开16次村民会议,换位思考乡亲们的所需所求和担忧,做通自家5兄弟的工作,一起认领了最边远的土地,175户耕作的254亩384块土地终于被置换整合为175块,5个村连片实现“一户一地”。 目前,阳山县2918个经济社同意展开土地整合,其中1639个经济社已整合土地面积18万亩,占二轮承包土地总面积的62%。土地实现“由碎到整”,全过程做到“零上访”。 “老百姓有老百姓的办法。”清远英德市九龙镇党委书记黄永晨也坦言自己“受了一回教育”。 汕昆高速清远段建设征地,涉及英德市九龙镇7个村52个村民小组共1758亩。去年7月一开动员会,黄永晨傻眼了:期限是40天。搁以往,要在这么短时间里顺利征下这么多地,不出矛盾纠纷不可想象。2005年市里搞一条航道疏浚工程,为征地补偿吵吵闹闹至今还没完全解决。 “现在跟10年前大不同,有村民理事会了。”这回,黄永晨并没急于进村量地数青苗,而是制作了一份委托书,发到各村各家各户,由他们签字委托村民理事会做征地补偿的全权代表。一个星期后,52个村民小组全都签了回来。 接着,镇里又召集各村理事会代表200多人,与镇政府干部组成工作小组。白天到田地,当着村民面现场点青苗、量土地,户主当场画押确认;晚上加班汇总,制成表格次日张榜公布。不到两星期时间,征地全部搞完。如今汕昆高速清远段已进场施工5个多月,没有收到一宗相关投诉。 “以往基层很多矛盾的产生,与政府自上而下大包大揽的管理与供给方式有关。政府一竿子插太深,影响了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积极性。政府能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管得好,有时就费力不讨好。”清远市委农办副主任赖志军深有感触。 赖志军曾任英德市西牛镇党委书记。作为清远全市3个试点镇之一,西牛镇探索将村委会职能下沉到自然村,推动行政与自治职能分离,农村矛盾纠纷随之得到有效化解,以往有名的“上访镇”,如今基本保持“零上访”。这一局面的扭转,赖志军归结为“政府归位、自治到位”。
小单元的大课题 “村民自治的第三波实践需要制度跟进” “办成一桩事,不知要吵多少架!”王廷翠的大白话里,透着自治落地的酸甜苦辣。 王廷翠是秭归县郭家坝镇王家岭村的老党员,也是第七村落理事会的帮扶员兼监督员。 “修路砍的柑橘树是大树,要给我换一样大的!”王廷翠记得3年前谋划修建果园路第一次开会时的情景,村落21户村民,来了16户,火药味十足。 “后来发展到连开会选个地点都要吵,因为见面就嚷嚷,谁也不愿意20多号人在自己家里吵得脸红脖子粗,生一肚子气。”无奈之下,王廷翠组织大家到村头的小树林里吵。“有次早晨7点开会,吵到11点散了;午饭之后,接着开,接着吵。”王廷翠说,这样吵了十几次,利益诉求充分表达、互有妥协,土地调整、柑橘补偿、筹资筹劳等问题终于达成一致。 修路对各家果树的影响有多有少,需要互相找补。王廷翠就带着一个人一棵棵数,数一棵绑一根绳,另一个人数一棵解一根绳,直到两人的数对得上才作罢。1.2万棵果树,足足数了一个星期。 王廷翠家里有几大本手写的修路流水账,每家应出工多少、实出工多少,村民集资收入多少、支出多少,每家损失了几棵树、谁补谁几棵树等,事无巨细,全都公布给村民看,经大家签字同意。“群众的事情,每个细节都要细致到位,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 “村落自治与农业生产发展相结合,让民主成为实实在在的东西。”专家学者指出,秭归也好,清远也好,划小村民自治单元的改革探索,适应了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有效化解了农村社会“神经末梢”管理缺位和失灵问题,为完善村民自治的组织结构和法律制度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清远、秭归的改革实践启迪我们,建制村并不是村民自治唯一有效自治单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院院长徐勇多次赴清远、秭归实地调研,他说,我国村民自治自发产生于自然村,定型在建制村,如今在广东、广西、湖北、四川的一些地方再度活跃于自然村,实现形式经历了三个波段。“村委会职能下沉到自然村或者村民小组,可能更适宜于自治。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自治单位愈小,自治范围和内容愈有限。”他建议,建构多层次多类型的村民自治实现形式体系。 徐勇提醒,清远也好,秭归也好,自治单元下沉,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有体制和现实难题:村民理事会自治组织职能有待明确,应提高行政事务准入门槛,防止重蹈行政化覆辙;自治运行资金有待充实,单靠群众筹资筹劳仍然捉襟见肘,应创新公益项目的实施,壮大集体经济;自治主体动力有待强化,目前自治行为都是义务服务,应创新“以奖代补”机制,保障村民理事会工作开展。 2014年和2015年两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在有实际需要的地方,扩大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徐勇认为,这不仅在于将自治单元建在什么层次,而在于提出了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命题。“村民自治是来自于村民的自我治理活动,同时又是一项国家治理制度安排。村民自治的第三波实践需要制度跟进。” |